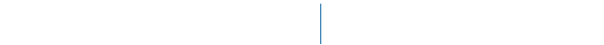紀念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德迪夫
本校董事長應《環球科學》雜誌邀稿,撰文紀念有細胞生物學之父稱譽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德迪夫,刊登於2013年7月號雜誌內容全文。
德迪夫與本校董事長情誼深厚,因長期受病魔折磨,於2013年5月4日在比利時選擇以安樂死的方式告別人間。
【環球科學雜誌封面】

紀念德迪夫
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德迪夫也在充分展現對生命的坦然與豁達的胸襟,
從人生的舞台優雅轉身謝幕。
2013年5月4日,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克里斯蒂安‧德迪夫(Christian de Duve)在比利時選擇以安樂死的方式告別人間。95歲的德迪夫在住家跌倒後,因為長期飽受癌症與其他健康問題折磨,德迪夫要求醫師執行安樂死,並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辭世。比利時是少數能合法執行安樂死的國家,而我也完全能理解為何德迪夫做此決定。向來獨立的德迪夫,總是樂於助人卻不願意成為別人的負擔。德迪夫是我赴美研究的第一個老師,回首塵封往事,與德迪夫的師生情誼與相處點滴鮮明地躍上眼前。
記得18歲時,第一次離開巴西並抱著興奮的心情遠赴紐約,期待在洛克菲勒大學展開我人生的科學探險之旅。甫到紐約沒幾天,立刻趕去拜訪景仰許久的德迪夫,希望他能擔任我的指導老師。那時德迪夫剛得到諾貝爾獎且在細胞生物學上已有卓然聲譽,但談話態度卻比一般人更加謙虛誠懇,提供一個年輕的研究者許多終生受用的珍貴建議。那天德迪夫不藏私地分享他多年研究的心得,真誠地分享著:「我離開比利時後,曾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和美國華盛頓大學進行生物化學的研究工作,後來到了人稱"科學麥加"(Mecca of Science)的洛克菲勒,不僅能做自己熱愛的研究工作,又提供我優渥的待遇,讓我深感幸運。」隨即語重心長地說:「我建議年輕人選擇一個有興趣的題目全心投入,只要有毅力地堅持下去,必然能有所成就。」
當時,德迪夫曾建議我考慮研究「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他的學生Carl Beyer是樹突細胞的最早發現者之一,後來我的好友拉爾夫•斯坦曼(Ralph Steinman)因確認樹突細胞免疫功能而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參見《環球科學》2011年11月《我的老友》)。迄今我仍印象深刻的是,在當天下午會談後,德迪夫立即搭飛機趕回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教授生理化學。由於對科學研究與教學工作的熱衷,德迪夫奔波於美國與比利時二地教書從不喊累。
德迪夫的建議著實讓我掙扎許久,後來考量到德迪夫的實驗室是以細胞生物學而非以免疫學為研究主軸,且指導老師德迪夫於二地往返而非全職任教於洛克菲勒,所以後來並未加入其研究團隊。德迪夫的實驗室位於洛克菲勒布朗克研究大樓七樓,後來我主持的分子免疫及細胞生物學實驗室在布朗克二樓。那些年,我常搭電梯上樓去德迪夫的實驗室長談,有時討論細胞生物學的研究發展,有時僅是老友話家常。
■ 細胞生物學之父
比利時裔的德迪夫出生於英國,於二次大戰期間擔任比利時軍隊的軍醫,曾被德國軍隊俘虜但順利逃脫至比利時。1947年於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教授生理化學,1962年起亦赴洛克菲勒大學成立實驗室,從此奔波於比利時與美國二地。1974年創立知名的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細胞分子病理學國際研究中心。因細胞構造的突破性研究,於1974年與阿爾伯特•克勞德(Albert Claude)、及喬治•帕拉德(George Palade)共同獲頒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克勞德開發離心技術以分離細胞結構,並發現提供細胞能量的粒線體(mitochondria)。帕拉德則證明了核糖體 (ribosome) 是蛋白質合成之工廠,並率先使用電子顯微鏡。德迪夫則運用離心技術使細胞結構一覽無疑,並發現溶酶體 (lysosomes)。溶酶體是動物細胞中用來消化養分及排除廢物的小球狀胞器,這內含多種水解酵素的單層膜囊狀胞器,能分解生命所需的有機物質,也能像垃圾處理場般對老舊損壞的胞器與細胞質進行分解,同時具有消化與排泄的功能。
在現代醫學認知中這僅是簡單的細胞生物學觀念,但在這之前,人們對細胞內的組織充滿未知。在他們三位發現細胞內的重要組成後,人們對細胞結構有了嶄新的認知。這些突破性的發現不僅奠立現代細胞生物學的基礎,更開創出嶄新的科研領域。因此,位於瑞典的卡洛林斯卡研究所(Karolinska Institute)諾貝爾委員會,在頒發諾貝爾生理醫學獎時,曾讚譽他們為20世紀的細胞生物學之父。何其幸運地,這三位傑出科學家-德迪夫、克勞德、帕拉德都是我的老師,三位良師益友在我的研究生涯提供許多鼓勵與啟發。後來克勞德於1983年辭世,帕拉德於2008年辭世,現今德迪夫也告別人世,細胞生物學的三大巨人相繼隕落,實為科學界的重大損失。
■ 活潑的教學傳統
成立於1901年的洛克菲勒大學,除了是知名的生物醫學教育研究中心,還包含全球第一個臨床研究醫院,提供研究人員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20世紀許多重要的科學突破都發生在其實驗室,因此也總能招募到全球頂尖的學者前來從事研究。每年招收學生不超過20個名額,入學後並非由老師挑選學生,而是由學生挑選老師。洛克菲勒以主題實驗室取代傳統系所,每個實驗室的負責人地位其實遠超出一般大學系所的系主任,其中有許多負責人得過諾貝爾獎或甚至更高的學術成就。我在擔任洛克菲勒入學甄試委員會委員時,曾延攬台大、北大、上海大學、協和醫院等地的優秀研究者,接觸當時內地最早一批到國外留學的醫師,其實有幾位也曾到我的實驗室共事。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值得回憶的美好經驗。
德迪夫在洛克菲勒是出了名的好老師,運用淺顯透明的表達方式讓學生輕鬆理解最新科學突破,其教學方式影響我很多。幾年後,我與1999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布洛貝爾(Gunter Blobel)共同開課細胞生物學十多年,便是延襲德迪夫的教學傳統。除了採用輕鬆活潑的互動教學,講師中有近1/3是由諾貝爾獎得主為研究生講課,實在要感謝德迪夫與許多諾貝爾獎得主在百忙之中撥冗投入講師工作。
我們的課程是當時校園中最受歡迎且規模最大的課程,特別是針對研究生的教學課程,透過歷時4-6個小時的馬拉松式講座及2小時的小組討論來進行。不僅變成洛克菲勒的課程典範,也被許多大學視為參考的教學模式。近年來,我在亞洲同樣在推動這種教學模式,包括台灣與中國。
■ 科學的黃金時代
我常與學生分享,40至60年代實在是科學發展的黃金年代。只要肯有毅力地堅持,各領域的研究都能有突破性的成果,且影響力能跨越各領域,不像現今的研究影響力僅侷限於單一領域。以我個人為例,在任職於洛克菲勒時,一股傻勁地投入「自然殺手」細胞的研究,研究殺手細胞如何消滅癌細胞或受病毒感染的細胞,後來解開自然界從高等的哺乳類到原始的菌類都是用相同的殺手細胞機制,這發現的確為當時的我帶來了些成就感。
事實上科學突破往往離不開心中的理念或藍圖。科學家有時就如同發明家,先有藍圖後再以「逆向工程」回頭去驗證理念而得到成果。有時,研究上的突破源自於技術上的發展,也就是說先有技術發展爾後才有研究突破。舉例來說,先有克勞德開發離心技術,運用高速旋轉所產生之離心力將液體中不同密度的物質予以沉澱分離,進而分離細胞胞器,並將生物學帶入次細胞的領域。同時克勞德與帕拉德成功地運用電子顯微鏡於生物醫學研究後,德迪夫運用離心技術與電子顯微鏡於細胞胞器研究才發現溶酶體。
即便如此,德迪夫在研究過程中還是面臨不少考驗。比如說,他發現了存在於溶酶體內一種磷酸水解酵素「酸性磷酸酶」(Acid Phosphatase,ACP)的特殊現象。在研究的過程中,如果使用研磨杵這種較溫和的方式來破壞細胞時,檢測出的酶活性較低;若是採用較激烈的方式如電動攪拌器來破壞細胞,則檢測出的酶活性較高。經過不同比對,才發現由於溶酶體外面有單層膜包覆,當這層膜被破壞時,酶的活性才能被顯現,如今酸性磷酸酶的活性檢測已被用來作為攝護腺癌等多種疾病的輔助診斷。
或許在現代醫學的角度這是簡單的檢測技術,但其實結合了先進的生化技術與細胞科學,也才有現今的細胞生化學(Cellular Biochemistry)。能結合細胞結構(structure)與細胞功能(function)二大領域,科學發展其實已邁入嶄新的階段。原本就是醫師背景的德迪夫,比一般人更理解到科學突破應該被運用到臨床研究,才能真正幫助為疾病所苦的人。
除了在醫學與生物學上的貢獻,德迪夫在研究生涯中,還主持了許多具代表性的研討會,1999年曾接受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委託主持研討會,探討在奈米菌理論中,最小細胞需多大尺寸能支持生命,當時那是個頗具爭議的題目。巧合的是,2008年我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的封面故事就是證明奈米菌並非細菌或會繁殖的生物體。事隔20年,與我敬重的老師在科學領域因奈米菌主題再度交會。
■ 最後一堂課
自獲頒諾貝爾獎至95歲辭世前,德迪夫終生奉獻給臨床疾病與機制,揭示許多遺傳疾病的途徑,對人類遺傳性疾病的研究貢獻卓越。除了醫學上的貢獻,德迪夫更以生命最後的歷程啟發我們。德迪夫不願成為家人的負擔而選擇以安樂死向世界告別,理性地等待美國的兒子五月初抵達比利時後,在四個孩子的陪伴下安詳地辭世。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德迪夫充分展現對生命的坦然與豁達的胸襟,從人生的舞台優雅轉身謝幕。我們何其榮幸從這位不凡的醫界導師身上,學習到生命態度的最後一課,也是最珍貴的一堂課。
發布日期:102年7月4日